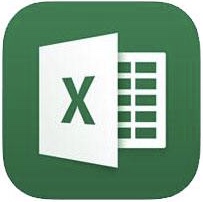新闻
国际快递查询-潘石屹对话柳传志:企业家要用进步的力量让法制更完善
新闻 | 2019-11-05 04:43编者按:《潘谈摄影间》是一档将潘石屹的两大爱好——“摄影”和“聊天”结合的访谈节目,由凤凰网视频出品、《财经》新媒体独家合作。在《潘谈摄影间》中,主持人潘石屹将透视的对象瞄准各领域的名人、大咖,通过访谈,洞察身处舆论热点中的名人的人生态度、文化观点,以及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。每期,《财经》新媒体根据采访视频整理成文,以方便读者阅读。
一无所有王健林、悔创阿里杰克马……“谦虚”大佬队伍里又增加一员——“女儿不行”柳传志。5月8日,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做客《潘谈摄影间》,与潘石屹进行对话。柳传志谈及儿女时表示,“儿子怕坑爹不敢公开关系”。谈及女儿柳青,柳传志笑称,“她本来也没多大能耐”。对此,柳青在微博上回应称:“论跟自己老爸搞好关系的重要性”,并表示“其实我觉得我还凑活”。
通过本期访谈,我们可以看到柳传志在父子、父女身份转换中教育观念的传承,还可以感受到过往经历对个人品质的形成作用,以及柳传志办企业时的信仰,把不在改革中牺牲定为信条,有理想而不理想化。
饿到吃银翘解毒丸
潘石屹:柳总,你们这一代企业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,对物质财富和市场经济独特的理解,后一代的企业家们或许不会再碰到了。我觉得把第一代企业家们的经历记录下来会非常有意义,今天您跟我们讲一讲您的经历吧?
柳传志:我1944年出生在上海,父亲(柳谷书)当时在中国银行上海总部工作,解放后被调到北京筹建中国银行总部的建设。记忆中,当时的上海很繁华,十里洋场;而到了北京后,感觉当时的北京和老照片里的北京一样,风沙大、街上有骆驼,有一种荒漠的感觉。
到了北京后因为家里总搬家,所以也断断续续换了好几所学校。7岁时,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子弟小学读三年级才算是稳定下来。小学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打架,我们当时是住宿制,班里的同学有革命老区来的,也有农村地区来的,当时最大的同学大我8岁,强生物流 ,经常有年龄大的同学欺负年龄小的同学。为了跟年龄大的同学抗争,我们会经常打架。到了五六年级时,我团结了一些和自己一样的孩子,才不再受欺负。所以,我对小学的记忆就是“混”。
潘石屹:住校的时候能吃饱饭吗?
柳传志:银行职工的子弟小学,伙食还是挺好的。1955年,我小学毕业,在这之前,我其实对中国整体的吃饭情况没什么感觉。那个阶段,感觉正是国家欣欣向荣的时候,抗美援朝胜仗也多,孩子们经常唱一些积极的歌。
潘石屹:您的童年是充满阳光的,而我那时候的回忆是吃不饱饭。
我1963年出生,正是全国最吃不饱饭的时候,有记忆的时候,西北还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,我们当时都靠领救济粮勉强度日。而且我们家还被划定成了地主成分家庭,领取的救济粮很多是发霉的红薯片。即使那样,拿回家后煮一下就吃了。一年12个月,我们家的存粮仅够吃6个月,不够时就去借,借到后面家里就真没什么吃的了,不得不把两个妹妹送人。其中,一个妹妹送到了陕西,又因母亲常做噩梦,后来才把妹妹给接回来。我们村当时有27户人家,最后,村里的27户家庭有17户趁着天黑逃荒到外地要饭去了。
柳传志:你最饿的时候饿到什么程度?
潘石屹:我的印象就是晚上一直流口水。
柳传志:你那时候还小,所以形容饿只能形容到流口水,我的形容会更深动。
1961年是全国饥饿最困难的时候,而我当时刚刚高中毕业,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,平常就完全是干熬。有一天晚上我夜里饿醒了,怎么也睡不着。最终拿了一片银翘解毒丸的药片放在嘴里慢慢的嚼,吃完后肚子非常的难受,一晚上烧的身上、头上直冒冷汗。
1961年下半年,我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,因为是部队,比地方粮食多。当时部队的馒头是一个切三刀,每人四两半的标准。食堂里有三口大锅,两千多人都冲着最稠的锅去。有意思的是,每个人拿的碗特别的讲究,碗小了不够吃,碗大了吃不了第二碗粥就没了。有时为了捞稠点的粥,人和人互相挤着,棉帽都掉粥里,大家装作跟没看见一样,照样把粥都喝完。
有一天部队会餐,提前通知说主食随便吃。很多人到了食堂后,先冲到了盛主食的地方,把碗满满的扣瓷实了米饭,后来到了桌子上才发现,每个桌上都放着三大脸盆菜和肉。当时又不敢剩下饭,一顿饭也整整吃了三个多小时。米饭是一勺一勺的塞进肚子里的,直到塞完最后一粒米为止。
郑重声明: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,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,多谢。
| 千航国际 |
| 国际空运 |
| 国际海运 |
| 国际快递 |
| 跨境铁路 |
| 多式联运 |